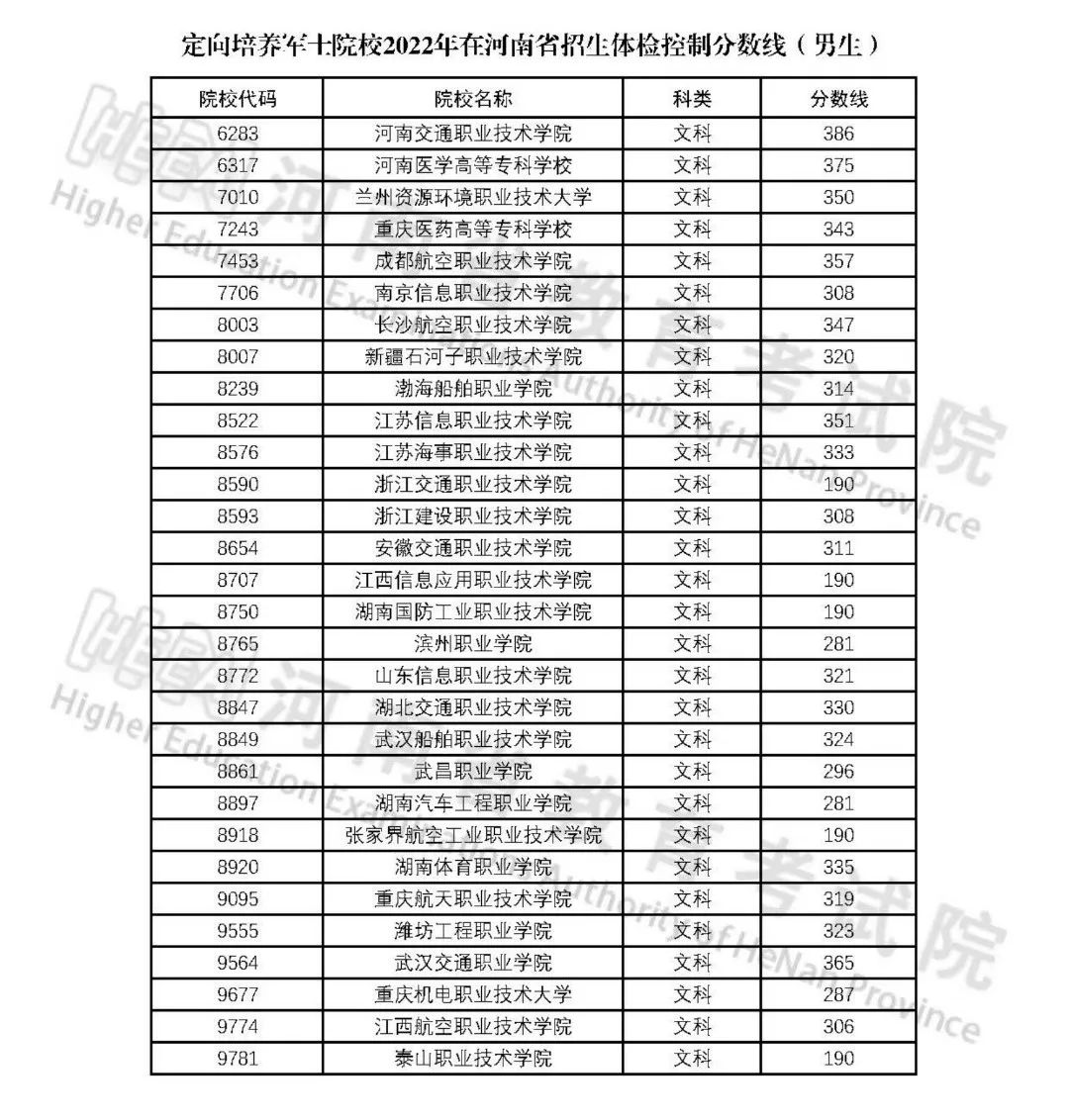《刹那》:一部精神赋格的生命交响乐章|热点评
【阅读提示】
《刹那》是当代女作家何向阳在病痛挣扎中创作的诗集。诗人以多个自我的反思、抵抗,寻找驱走黑暗的原动力,却发现“黑暗”是一种邀请或启蒙,疾病“囚禁”的只是“我”的身体而不是灵魂,创造了一个“你就是你所创造的宇宙”的精神美学时空。这是一部救赎之书,更是一部希望之书。
何向阳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作者:王红旗
何向阳的诗集《刹那》,是诗人被疾病狂飙卷入濒临生死抉择极地之时,“立虹为记”、自我拯救的灵魂“夜航”。诗人把评论家的智慧,散文家、诗人的性灵,以及女性的生命之爱与关怀融汇在一起,携带真诚与善良、美学与哲思、博弈与“中和”的文化基因,结合“万物共生”的本然思维逻辑,以从未经历过的“引体向上”的强劲生力,以生命诗画与自然之乐为航梯,心脉流转升华为翼翅,接通人类文明初始源头的宇宙诗心,随着精神与自然时空循环往复的更替,聚集一次次生命瞬间内觉,深悟人的个体命运“无常”之理。可以说,《刹那》是以多重复调的抒情性叙事,形而上之多部和声,创构了一部精神赋格的生命交响乐章。
创构从“瞬间”到“永恒”的精神美学时空
从《刹那》的整体结构看,诗人承继中国诗画同源、仰观俯察的审美传统,以灵魂“夜航”的精神旅程为序,以似断似续的断句体式,多层“潜结”记忆的共时节奏,连缀成了百章千行的诗歌长篇,并嵌入亲手拍摄的35张彩色画面。诗与画多样“留白”手法的相互映衬,多种色彩变幻与情才意蕴的叠层显现,和着天籁之音的玄妙神韵,诗化出“腾踔万象”的审美意境。“至甜”“最苦”“品尝”“记住”“遗忘”等断句,几乎贯通其整个生命长河流变的情感体验,诗人将自我生命不同时空的记忆瞬间,提升为“思接千载、视通万里”的精神美学速度之广远。不仅裸呈诗人一个个生命瞬间辉耀、灵魂腾挪、精神翻飞之轨迹的多层次元,而且可以感知到一种特定时空情景与人物精神心理“互答”汇通的深层旋律。
如果说,诗人生命千思万绪的瞬间顿悟,流淌出的每一首小诗,是“长长隧道的一束束亮光,让我看到的不只是隧道中长的暗的现实,更是暗黑隧道外不时闪现的光芒与明媚的召唤”。那么,诗人亲手拍摄的每一幅画面,犹如自我精神生命深度体验的一幅幅心灵画像。此可谓诗人向海天深处、无染灵台,寻找根源性光明,攀缘跋涉求索的精神航道之隐喻。诗人以一位“觉醒者”的自觉,从探究“水追逐着水”眩异呈奇的混沌初开,到回归母腹“再生之水”的婴儿初我,其深层意识和彩虹、太阳、银河、群山、神树、雪峰、海洋等“永恒存在”紧密相连,仿佛自然万物闪射着自足富有的光芒,朝着诗人精神生命之诗的“轴心”凝聚,在自我生命与自然相融的过程中,形成了包举诗心天宇的大圆,昭示灵魂“夜航”之终极目标——重生。
暖阳下的枯蔓衰草,被酷寒冻裂的黄土地,冰河融化成一个个圆形的连环,万木凋零的另一种绚烂;无眠的海上,连接云涛的雪峰,墨色的模糊阴影,不忍沉入海底的炽银之斧,可以扭转一切的混沌;无岸的水下,一串串脚印似的人生小道,一条伸向天际的隐约之路,深藏于根茎里的生命,形态各异的心途迷宫,漂浮着如一张张薄纸片似的灵魂。这些相互冲突而又混融、不断变形的“人情化”的自然意象,表现出诗人“以造化为师、以真为骨、以美为神、以动荡的社会人生为源、以人间的喜怒哀乐为怀”的精神体验。这种强烈的生命精神意识,从自我主体透升的神圣崇高与诗意壮美,将“瞬间即逝”的无穷动之景,定格为心灵内海的一种“永恒”精神实存。
扉页诗“立虹为记”和第一幅照片“向高山举目”的叠现,天边挂着一弯七色彩虹,高原雪峰映在海天一色的水中,露出破碎的神秘明丽与暗花,可以说是诗人内在时空“从黑夜走向白昼”顽强意志的象征。诗人写完诗集后记,“我面前出现的一道彩虹,现实中不断地与之相遇,仿佛神启。2016年5月23日傍晚,术前一天,它出现在北京上空,我在协和病房中仰望着它,心生感慨……心中的虹又哪里会沉入黑夜。”诗人以宇宙自然的“瞬间”显现、重复出现而“永恒”存在的虹,暗喻其心灵微宇宙曾反复出现而不会沉入黑夜的虹,象征诗人病痛中坚定的生命信念。诗人的灵魂“夜航”与极目“云霞明灭或可睹”的记忆相交织,以死亡连接新生,以绝望连接希望,向天地“大声吟诵”的精神歌唱。
开拓从“至暗”到“澄明”的精神重生之路
《刹那》开篇“群山如黛/暮色苍茫”,暗示灵魂“夜航”之日暮途远,渐渐“至暗”的夜,已露出“狰狞的面容”。这是诗人遭遇一连串生命“至暗”事件的隐喻:“2016年5月6日,我和哥哥赴青岛将母亲的骸骨安葬大海,完成了母亲一直以来海葬的遗愿。24日我确诊乳腺结节并做了局部切除,30日出院。当天父亲体检结果不好,6月24日父亲确诊胰腺占位早期,当天我手持电话,一边嘱托友人应对困难,一边应对自身病痛,心绪已然跌入人生的最谷底。父亲月底来京,多方论证后于7月12日手术并于25日顺利出院。两个月来的身心磨折,或是成就这部诗集的关键。”诗人在生命不堪承受之重的心境下,从自我身体病痛,体会到家庭之爱的血缘亲情,延伸至对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诚情信爱。
诗人认为,人的个体生命只有与宇宙自然相和谐,才有可能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爱。诗人听从当今几乎被遗忘、被遮蔽的地心之声——原型母亲爱的召唤,以瞬间叠现无处不在的“巨灵”,即肉体血缘的母亲、文化血缘的“原型母亲”与自然血缘的“宇宙母亲”的精神联合体,其匍匐的无极大爱之包容、和谐大美之精神,不仅将诗人“至暗”的灵魂“夜航”之路,照耀为一种“澄明”的通过仪式,而且对当下“物质时代”人类失去爱的灵魂,具有普适性的救赎意义。
诗人对儒道先贤“内圣”的人格理想、“性心德行”的澡雪精神的智悟,形成一种反复求诸内心的生命美学创作理念,认为人的生命历程本来就是一个一个相连的“重生之圆”。其书写身体记忆,“第一刀四十三岁落于子宫/第二刀四十五岁落于腹部/第三刀四十九岁结印左乳。”绝非只是言说疾病身体的疼痛,而是对生死彻悟的乐观与豁达,具有极其深刻的生命洞见。诗人灵魂的“夜航”,不仅找到生活中最本真的自我,而且回到了温馨的日常生活状态。在一切安详宁馨中,“我看见我坐在一座明亮的大房子里/在阳光照彻的书桌上/笔尖的句子奔涌而来”。“选择性”记忆片段的诗性叙事,不仅表露出诗人在身体病痛最痛苦时刻,以最健康、最理想的精神飞翔,“重建生命”的自我灵魂样态,而且更表现诗人重建人类“心上”殿堂的济世理想。开拓出一条从“至暗”到“澄明”的精神重生之路。
诗集《刹那》重要的审美诗学贡献
首先,呈现诗人在“生命中最艰难、最灰暗也最残酷的岁月”,面临疾病向死亡逼近的寂灭性威胁,以“不一样的精神”,自下而上驰情飞向充满精神的天空,面向宇宙母亲敞开心扉,一场“天人之际”的交感对话,探寻到一种消解自身病痛的“本心之药”,一条“光明如初”的重生之路。虽然疾病是人最切身丧失多重自我的“异化”形式,但是当患病的身体里健康向上的灵魂,焕发出美妙绝伦的闪光精神,生命却表现出一种“非常态”的创造性。这种精神抵抗之美,使诗人超越文化既定的女性“柔弱之美”,重获一种战胜疾病的内在生机活力,确证“无常”只是生命“常态”的一个变奏,人类完全可以自己拯救自己。
其次,诗人自觉面向天地之心的精神吐纳方式,探源人类存在的“精神原型”——宇宙母亲。以一位隐形“叙事者”的精神在场贯穿整体诗脉跌宕,呈现诗人把接踵而来的生命苦难,锐化为一种内心永恒的精神梦巢,从自我遍体鳞伤的身体里,生长出自由飞翔的翅膀。以山川日月星辰万方乐奏,升腾起一个与身心共存、与日月同辉、永葆爱与美生命精神的“母神群体”。诠释人类任何强韧与美好的生命状态,都源自内心涌出的强大精神信仰。深寓对当代人被繁华物质遮蔽而失去爱之灵根的精神症候,以小诗微言大义的神思灵光,开出回归性的灵魂“夜航”“修心”的救治良方。可谓一部富有人类性价值的涅槃之书、救赎之书,更是一部希望之书。
(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)
- 深圳证监局召开北交所高质量发展证券公司座谈会|今日要闻 2023/05/23
- 韩国烤肉怎么做_韩式烤肉家庭自制做法分享 2023/05/23
- 【世界速看料】欢瑞世纪收年报问询函:说明营收增长销售费用下降的合理性,说明新增综艺业务的业务模式、盈利模式、收入确认模式 2023/05/23
- 一年十个小目标,玩转估值不是梦 天天微资讯 2023/05/23